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
0546-8956908
咨询热线:
SHANDONG QIZHENG LAW FIR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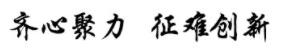
法治中国之我见
来源:
|
作者:qizhenglvshi
|
发布时间: 3129天前
|
4650 次浏览
|
分享到:
单位: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 作者:齐彬礼
内容摘要:从世界人类治理国家的发展史上看,法治国家的治国方式是比较先进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当口,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决定加快法治的进程,不但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必然在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本文谈建国以来法治发展的过程,论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影响和作用,诚与律师同仁共同增强法治思维。
关键词:法治的概述 法治的发展 法治的作用
曾几何时,权大还是法大、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争论不休。从一般意义上讲,法是一种人造工具,法治只是治国的方式之一。权力也是一种治国方式,且人的权力直接行使后的效率比较高。在一般情况下,用权力创建政绩,往往比用法律创建政绩要快得多。还有,道德是一种辅助的治国方式,强调道德准则对依法治国的指导和补充作用,确立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也是必要的。实践证明,法权结合、法德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综合的看,我国目前的治国方式呈现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政法”状态。战国末期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推崇“法、术、势”相结合,三者并用的法治思想,蕴含之意在治国理政聚民中,法不是唯一的手段,有法,还需有权的人保证实施,如果不能保证实施,须动用武力强制实施(如军警镇压)。人类历史上凡是主张依法而治的国家或民族都十分注重弘扬法的精神,以唤起人们的热忱,使依法而治由少数决策者的思想变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对于法的价值,西方奉为政治信仰,中国作为政治工具。但中西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奉行深藏在实体法背后的最高价值本体,公平正义,确立法律在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巩固政权。迄今,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章;]。那么,中国发展到今天,为什么执政者强烈地推行依法治国方略呢?笔者沿着建国以来法治的兴衰脉路加以分析,或许能够有所提示。
一、推“四大”无法
从战争年代进入建国初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闭门锁国和文化知识的局限,中国的老百姓大多不知道法是什么概念,更不知道法的作用和适用的重要性。他们只是虔诚地企望一个神圣人物来引路导航,像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西方上帝式的“救世主”。于是,就出现了红太阳式的伟大人物毛泽东。这个英明领袖确不负众望,已经考虑到了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在巩固了政权后,即亲自主持制定了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54宪法),试图构建起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他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说: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1日,第129页;
]领袖的话没错,然而,法律不仅是由当权者的顶层设计,关键是上行下效地坚决执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政治上的党内斗争和阶级路线斗争的需要,毛主席深感法律对他的制约太大,不利于实现其政治意图,就以法条太多难想难记为由束之高阁。他的理论依据是: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后来直接挑明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此话虽然在出处问题上有过争议,但客观情况确实如此)。于是乎,从1957年“整风反右”中提炼出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就成了法的主要形式,后来被写进了1975年《宪法》(有人称“文革宪法”)。毛泽东本人带头写了一张“大字报”登在中南海,自然“红卫兵”组织层出不穷、“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如火如荼、“最高指示”言出法随、“文攻武围”战斗升级,政治局面陷于混乱。虽然道德教化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可基本的社会形态是人治大兴其道,冤假错案频频发生,一个泱泱大国陷入了无法无天的境地,创造了世界上比较典型的人治社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才得以缓解。由此,人治带来的恶果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二、审“两团”复法
十年“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呼声遍地。但是,要治理好一个国家,首先解决的是政权的稳固问题。经过党内激烈斗争,“四人帮”终于败下阵来成为阶下囚,面临当局的处置。适逢谋害毛泽东主席未遂而折戟沉沙的林彪手下干将们被羁押多年,也需作出历史的评判。于是,当局就将林彪的人马和江青的人马定性为两个反革命集团一并进行政治清算。可是,林彪早已死亡,江青是当年的“第一夫人”,尽管罪大恶极,若杀之将难以向躺在水晶棺中的伟大导师交代,还要顾及国际影响。若按党规党法处罚没有相应的条文遵循,也失之太轻。斟酌再三,还是对他们进行司法审判更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也能被国人所接受。可是,当时的司法审判程序和定罪量刑无法可依,即时立法很不现实。只有在法律的废墟上寻找有用的内容,参照前苏联的教科书,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应急之用,同时制定了《法官组织法》、《检察官组织法》、《律师暂行条例》作为配套法律适用,并迅速恢复了公检法队伍(由于未成立司法行政机关,律师暂由法院代管),设立了基本的政法框架。以此为基础,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分别组成了特别法庭和特别检察厅,以指定律师辩护的形式,搭建了控辩审三角形的审判架构。以“纠问式”为主的审判程序,于1980年将活着的“两团”人员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分别予以定罪量刑,以法的形式结束了这场党内斗争。同时,也成为历史拐点,开启了中国法律的制定,推动了以刑事法律为先导的“复法”运动。自此,中国进入了人治与法治的双轨制时代。
三、图“经济”造法
中国历来以“左右”分派,以“社资”分性。“极左思想”根植人心、束缚人脚,使人墨守成规,思想不得解放,人类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难以释放,社会文明的发展依然缓慢。可是,人类要发展,社会在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于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标准”问题成为“导火索”,使“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理论交锋,几经口诛笔伐,“改革派”终于占据上风。人心所向,“铁血宰相”邓小平掌握了最高权力。自此,中国的政治方向定调为“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的行动纲领是改革开放。在封闭了多年的国门被打开后,商品经济主体的思想禁锢被打开,国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各条战线出现了经商热潮。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和新的法律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服务于经济基础,可立法却明显滞后,使国内商品交易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得不到法律准确调整。尤其是外国人,在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前提下,他们不会轻易投资。然而,当时中国的民商事法律基本没有,有的就是台湾国民党的遗产“六法全书”。再沿袭传统立法体例中“诸法合体,重刑轻民”的习惯远不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于是,人大即组织法律专家、学者走出国门、引经据典,修订律例,结合国情,制定了大量的民商事法律和涉外经贸法律。加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各部委制定的规章及地方立法,初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为主体的民商事法律体系。由于是为发展商品经济,对外开放贸易自由开辟道路而强烈呼吁的产物,尽管这些法律法规及规章条文较粗,有的是现拿的“舶来品”,可这种造法数量之大、速度之快、实用性之强,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属罕见。以至于当时统帅立法的彭真委员长被誉为晚清时期“以律鸣于时”的法学家沈家本。也为日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求“维稳”变法
在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上非一帆风顺,矫枉必然过正。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可社会治安秩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恶性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甚至劫机事件层出不穷,打不胜打,出现了好人怕坏人的怪现象。究其原因,除去国民法治观念淡薄、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外,客观上大批回城知青和大量的社会待业青年的出现,使社会游荡人员增多,当时的价值观、信仰观出现危机,基层基础工作和党务工作疲软、自治管理滞后,政治思想工作教化乏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尤其指出的是,有些高干“衙内”为非作歹、顶风作案的作为,产生了及其恶劣的影响。若不打击,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阻碍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好形势,损害着国家的国际形象。于是,当政者借用古人“治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方式,决定从重从快从严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后的“严打”),从组织上加强了公检法队伍的力量,管理上扩建了多个劳动场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共同定罪量刑,甚至有的律师还要参加抓人(笔者亲眼所见)。在处理程序上,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可以不受诉讼法审判期限的限制,上诉、抗诉期限由十日缩短为三日,量刑时一律顶格判刑。继而,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高干子弟和黑社会组织的头子以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在国家强制力量的骤然打击下,遏制了犯罪的高发势头,顿使好人扬眉吐气,整个社会环境得到净化,社会治安趋于平稳,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严打”战役重点进行了三次,持续了20多年的时间。由于“严打”是特殊历史时期进行的非常之举,系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且忽视法律程序,使公检法三机关相互监督制约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未能限制住功利驱动下的刑讯逼供现象发生,在重刑主义的指导下,忽视犯罪人的人格尊严和辩护权利,为日后产生冤假错案埋下了伏笔,已成历史遗憾,只能进行反思。
五、应“接轨”善法
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大循环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在经济体制上,中国毅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模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博弈之中。与此同时,中国顺应国际法治的潮流,加入了世界法治一体化的进程之中。随着近现代人权思潮和人权运动的不断发生,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面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广大民众的民主政治诉求与法治思想的觉醒成了推动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尤其在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声浪中,执政者顺应民意,适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写进了修正的根本大法中。自此,“法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具有了突出的地位。由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我国不能搞“议会制”、“两院制”、“多党制”式的三权分离政治体制,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难以规划。可是,经历了“冷热”法律程序的洗礼,现行的法律制度明显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数量上虽然不少,但有些法律质量不高,在立法思想、立法技术的先进性上远不及发达国家,必须尽快赶上。于是,立法者对原定的法律法规重新梳理,分别进行“废、改、立”,并且在观念、制度、司法运作各个层面同时进行。在民商事立法上,对涉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进行了开放式的修定,使之更加适应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需要。对金融、税务、保险、电力电信、土地、计算机网络、企业破产等法律法规作了突破性的修改和完善,使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性。在刑事立法上,注重人权保障,确定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先进理念,提前了律师辩护的介入时间,设立了防止刑讯逼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了控辩双方“武装力量对等”的抗辩式庭审制度等。在行政立法方面,扩大了“民告官”的受案范围,加强了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严肃了办事效率,完善了行政执行,促进了政府的依法行政。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修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要完善立法计划,突出立法重点,坚持立改废并举,提高立法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习总书记已为今后完善法律制度做出了引领性的指示。[ 参见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第一版,第144页。]
六、固“政权”扬法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艰难发展之路,经过37年的励精图治,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效果,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财政大国,为“太平盛世”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自古以来就难以医治的社会顽症却膨胀起来了,那就是官员腐败。从人员上看,从村长到国家领导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数量上看,几乎所有的手握实权的大小官员;从范围上看,几乎涉及到各行政机关单位及各行各业;从数额上看,从5000元(贪污贿赂刑事立案起点)到成千上亿地贪占;从表现形态上看,由个人贪腐发展成家族式、窝案式、宗派式的利益集团,有的重大利益集团还有自己的保安和武装力量。随着现代网络的迅速传播,民众开始触目惊心而愤世嫉俗,后来见怪不怪,甚至感觉将腐败透顶,难以救药。严酷的现实是,这种腐败的蔓延,不但吞噬着国民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严重威胁着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这种严峻的挑战直接考验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平心而论,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学生们矛头直指官吏腐败动机良好,事件中被坏人利用酿成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非他们所愿。然而,“六四事件”定性之后,政治权力得到了稳固,经济建设顺利推进,腐败行为却有恃无恐,愈演愈烈,以致积重难返。联想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整党,整出的问题秘而不宣,高举轻放,走了过场,结果助长了腐败之风一发而不可收,以致养虎为患。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面对大面积的腐败,成千上万地抓杀实属激进,再小打小闹地惩罚已无济于事,必须大刀阔斧地整治方能见效。然而,治标不治本,整肃毕竟是手段,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毒瘤,必须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预防监督贪腐的“金科玉律”。可是,握有实权的人均不愿被人监督,再好的制度也得由人去执行,监督者仍须被监督。随着纪检部门监督权的实施,有的纪检人员经不住金钱的诱惑;随着贪污贿赂案件的增多,有的检察官成为金钱的俘虏。就有人提出“制度腐败”这样一个命题。但是,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宝塔式”结构,塔顶上的人主要靠自我监督。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呈“三角式”结构,相互制衡。然而,西方体制只可借鉴,不能照搬;要立足国情,顶层设计。斟酌再三,唯有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功能最大。于是,执政者高调推出“法治中国”的方略。 至此,依法治国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
注释:(1)参见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章;
(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1日,第129页;
(3)参见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2014年10月第一版,第144页。
(5802字)

